
过去的几周是圣诞假期,整个学院都格外安静。我的新年夜和圣诞夜并无两样,都是在台灯下继续自己的Draft。空荡荡的宿舍楼既可以让自己静心思考梳理每一条结论的脉络,也会让思念在某一个阴郁的午后像窗外的蔓藤一样缠绕伸展,寻不到根源,也看不到尽头。当我给导师发送完新的Paper纲要,邮件显示2020年1月1日00:28时,我才似乎真切地感受到又是一个新年开始了。元旦后第一天,感觉自己要有些仪式感来迎接这个新的Decade,于是决定到 Fitzwilliam Museum (菲茨威廉博物馆)去看看我在剑桥的那些挚爱。从宿舍楼出来,经由Downing College(唐宁学院)的后门,走过一段寂静的小路,几分钟后就能看到这座200多年前建造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了。作为剑桥大学的艺术和文物博物馆,Fitzwilliam 拥有超过五十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既有古埃及祈求通向永生的镀金棺具,中世纪时期极尽奢美的彩色手抄本,文艺复兴时期兼具思想与力量的雕塑,也有包括提香,莫奈,德加,雷诺阿,毕加索,伦勃朗和塞尚等的绘作。总之,对我而言,这里就是一个探寻未知与宝藏的乐趣之地,无论以何种心境来,它都能给我带来欣喜。
(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

Momentary or Permanent?
尽管藏品丰富,但我最挚爱的还是二楼的印象派法国馆。在这里,艺术家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脱离了以往对历史和宗教的依赖。他们主张到户外去,在阳光下作画,用油彩和眼睛去记录瞬息间光与色的变化,而眼前这幅莫奈(Claude Monet )的“Poplars(白杨树)”正是对这一主张的重要探索与诠释。1891年那个夏天,51岁的莫奈对河边的白杨树倾注了全部的身心,它们沿着河岸曲折,远远望去,呈现出很优美的S型。他希望通过同一片白杨林的系列组画来体现不同天气,不同光线,不同季节的光影世界里的变化。据说莫奈开始绘制不久,就被告知这些树木已经被卖给当地木材商,并将很快被砍伐。为了能够保持同样的树木数量同样的造型,他不得不和木材商达成交易,买下这片白杨,待他完成系列后,再还给商人砍伐。
莫奈经常独自一人划船,从他的Giverny花园沿着埃普特河 (River Epte)到上游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这些白杨树的所在。小小的木船是他的河上工作室,船底加了隔板用以储藏更多随时备用的画布。据莫奈的朋友回忆,很多时候,作画时光色明度差别变化的相对存在时间不超过7分钟,这也就意味着尽管莫奈拥有极度敏锐的视觉观察能力,他仍需要日复一日的划船停靠到同一个地点,以同一个视角在相似的光影条件下去捕捉那个笔刷下稍纵即逝的瞬间。就这样,到第二年年初时,他一共在这里绘制了32幅白杨树,并将其中15幅在1892年3月巴黎的首次个展上一并展出。莫奈用创新性的技法从自然的光色变换中描绘出富有节奏的瞬间,这次画展不但极大提升了他作为印象派领军者的声誉,更被评论家定格为“改变现代艺术进程的一个重要时刻”。一方画布中的白杨,有午后的清香弥散,日落里的柔和安闲,清风中的低声倾诉,阴日里的缄默不言,夏日里的郁翠成荫,也有秋日里的流金盎然。莫奈用色彩来度量光线的强弱,让这些静谧伫立在厄普特河边的白杨焕发出无限光彩。

(莫奈Poplars系列,1891年)
对我而言,每次站在这幅画前,它都能让我瞬间平静下来。感觉我和莫奈一样,站在一尾小小的木舟上,停泊的地方是一片浅浅的池沼,船头处是散发着夏季味道的软黑淤泥和水中婀娜的轻柔水草。抬头仰望那片白杨,等待阳光一格一格爬升,叶片一帧一帧泛亮,枝桠一寸一寸摇曳,倒影一帘一帘层叠,生长。慵懒的风在蓝天和浮云间徜徉,在宽阔的树冠间摇摆,在舞动的蒲苇间荡漾。慢慢地,远处的晴空朗朗,脚下的河水淙淙,岸上的青草悠悠都幻化成迷离的色彩与流光的纹样,没有了枝叶的繁茂,没有了躯干的挺拔,没有了河岸的弯曲,只看得见团团簇簇的笔触,只看得见葱葱茏茏的物形,只看得见蜿蜿蜒蜒的光影融汇,溢彩交织的瞬间印象。这一瞬间,仿佛是耳边拂过的风,是空气中掠过的香,是面颊上洒落的光。

(菲茨威廉博物馆-莫奈作品)
Truth or Vision?
是真实还是幻象?
离开印象派画馆,沿着长廊走到中庭,在最右前方的角落里有两个用酒红色的毡毯覆盖的玻璃展柜,很不起眼,若不是为了寻它而来,恐怕很轻易地就会错过。而如果当你看到展柜旁边的墙面上同样毫不起眼的展品名牌时,你一定会像我一样怦然心动。没错,名牌上清晰的写明:John Keats: Presence and Absence(约翰•济慈: 存在与不存在)。作为英国最杰出的浪漫诗人作家之一,济慈才华横溢,然而与他细腻华丽的诗篇不同,他的人生短暂而忧伤。济慈8岁时,父亲因坠马导致颅骨损伤去世,14岁时母亲死于肺结核,那个秋天,济慈离开学校到外科医生哈蒙德(Thomas Hammond)那去做学徒。19岁时,完成学徒,考入了当时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成为一名医学生,不足一个月后,他便已在医院内协助其他医生进行手术,并很快在一年后获得了专业医师执照。但这时他也深受困扰,是顺从他的心去潜身写作还是为了改善窘迫的家境去选择从医?如果当时济慈选择了后者,不知道他短暂的人生是否会感受到更多美好。

(菲茨威廉博物馆内济慈手稿展柜)
俯下身透过玻璃板,我认真辨认眼前手稿上的每一笔勾画,济慈惊人的想象力像一束耀眼的光在辽阔高远的时空中穿行,那璀璨里既有他熟稔的古希腊传说中百转千回的诉说:忘却世间忧愁的冥府烈溪水、众神聚集的赫利孔山上(阿波罗和缪斯诸神常居之地)的灵泉,还有歌声嘹亮世代不朽的永生之鸟;那璀璨里也有他敏锐独特的感官触角去传递的清新大美自然:山毛榉的绿叶、即将凋谢的紫罗兰,还有缀满了露酒的麝香蔷薇。那一行行隽永的写意,一笔笔细腻的独白,仿佛带我踏入了那个晴朗的春日上午:花园中有棵粗壮的梅子树,布满苔藓的黑褐色树桠上点缀着几丛鲜绿的多刺嫩枝,济慈独自一人静静坐在树下,交叉的腿上放着一本诗集,上面是几页草纸和一小瓶墨水。他紧握蘸水笔的手指上和指甲缝隙里是黑黑的墨渍,细细的笔尖在纸上窸窸窣窣划过。不远处的夜莺还在歌唱,那美妙如丝的旋律宛若空谷幽兰,眼前这清空恬淡的寂静早已幻化成他脑海中那至真至美的意象。在这个文字建构的虚幻世界中,他用华彩瑰丽的语言和摄人心魄的想象让我们和他一起去看,去听,去触摸痛苦与欢乐之间的挣扎,去体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抗,“花神、舞蹈、恋歌、欢狂”;“青春、苍白、消瘦、死亡”。他卑微的出身,贫疾的境况,都加重了他对死亡的担忧,但也焕起了对爱情的相守与渴望。1820年春,济慈第一次咳血后病情迅速恶化。1821年春,25岁的济慈终逝罗马。无论这份美是真实还是幻像,济慈短暂的人生都因这灼热燃烧的激情而像他仰望的星一样明亮。

(菲茨威廉博物馆展品-济慈夜莺颂手稿)
Exhibits or Emotion?
轻轻盖好展柜的布毯,我转身沿着长廊一路走下去,推开尽头的木门,眼前的一切让我有些诧异:这个小小的展厅是博物馆的Octagon画廊,而现在四周的墙上挂满了色彩各异的孩子作品,只有正中心的位置还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Jacopo del Sellaio的那幅《丘比特和普赛克Cupid and Psyche》(作于1473年,讲述了凡人普赛克Psyche公主嫁给爱神丘比特Cupid的故事)。看过介绍才了解,原来这是名为“激发2020 (Inspire 2020)”的学生作品展览 。在过去的12个月中,数百名当地小学生与他们的老师或父母一起来Fitzwilliam参观,他们被鼓励用深入、有思想的视角去观察这幅画,并通过思考和探讨去绘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然后博物馆选取一些作品展出,并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创造力。

(菲茨威廉博物馆- Inspire 2020)
我饶有兴致地认真欣赏这些小小艺术家们奇思的天马行空,展览中一个名为维奥莱特9岁男孩的作品深深吸引了我,他受原画的启发,绘制了名为“翅膀Wings”的系列作品,在作品介绍中,他说:“我的作品灵感来自于原作中丘比特的翅膀。我们参观时,看到的其他画家的不同笔触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例如我很认真地研究了毕加索画作中翅膀的运动,这确实对我的画非常有帮助。为了达到更鲜艳的色彩效果,我还将水彩和广告颜料混合后使用。和开始的计划与练笔相比较,我最终的作品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点羽毛的间隔。我的素描水平还需提升,但我对自己作品中的用色技巧很满意。”

(菲茨威廉博物馆- Inspire 2020,Violet,9岁)
让我感受更深的是一位叫做玛蒂尔达的9岁女孩,她在参观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到Fitzwilliam博物馆参观给我很大启发- 让我明白,艺术不仅仅是一件物品:它是一种情感;它描绘出了画家的感受,所以博物馆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有机会体验历史并留下回忆。”

(菲茨威廉博物馆- Inspire 2020,Matilda,9岁)
是的,我们看到的每一件展品,都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一段过往,而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一份坚定的信仰。读诗时,我们在字块间想象色彩;看画时,我们在油墨里揣度主张;透过他们的眼,我们看到了更美的世界;聆听他们的心,我们触到了更真的渴望。英文中“博物馆”一词为Museum,是从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Muses)的名字而来,所以博物馆的本意是“缪斯的崇拜地”,或“与缪斯对话的地方”。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每次看完这些展品后,都能感受到内心的充盈和向上的力量。无论你的缪斯是谁,无论她在何方,在这新的一年里,愿我们都可以成长为自己更爱的模样。
新年快乐!
2020年1月2日 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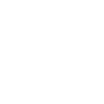










 手机二维码
手机二维码 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